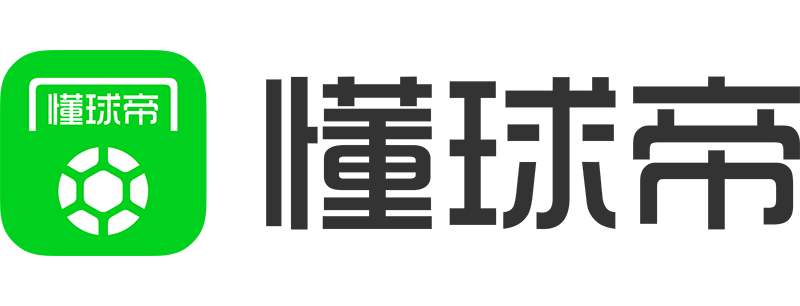贝拉希诺:我刚到英国时找不到我的妈妈,我被安置在一个寄养中心
那一年我独自一人来到英国,心中充满期待与不安。我原本以为母亲会在机场接我,然而当我走出希思罗机场时,在拥挤的人群中反复寻找却始终没有看到她的身影。那一刻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迷茫,手中紧紧攥着一张写有她地址的纸条,却不知该去向何方。
由于年龄尚小且没有成年人陪同,机场工作人员注意到了我的情况。他们尝试联系我的母亲但电话始终无法接通。随后我被临时安置在机场的一间办公室内,等待进一步安排。几位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轮流陪伴我,他们的语气温和但掩不住事务性的匆忙。我看着窗外陌生的天空,心里涌起一阵阵酸楚。
几个小时后我被送往伦敦郊区的一个寄养中心。那是一座看起来有些年头的维多利亚式建筑,门口站着一位名叫玛格丽特的女士。她自我介绍说是这里的负责人,语气平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。我跟着她穿过长长的走廊,注意到墙壁上贴着许多儿童画作,色彩斑斓却莫名让人觉得忧伤。
寄养中心里住着十几个不同年龄的孩子。有的看起来只有五六岁,有的则已经是青少年。他们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我这个新来的伙伴,但很少有人主动上前搭话。我的房间在二楼尽头,里面放着两张单人床,靠窗的床上坐着一个看起来比我稍大的男孩,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继续摆弄手中的魔方。
第一天晚上我几乎彻夜未眠。窗外的月光洒在地板上,形成斑驳的光影。我躺在床上想念母亲,想念家乡熟悉的一切。隔壁房间偶尔传来压抑的哭泣声,不知道是哪个孩子也在思念亲人。我紧紧闭上眼睛,努力不让泪水流下来。
在寄养中心的生活有着严格的作息时间。每天早上七点起床,八点吃早餐,九点会有老师来给我们上课。下午是自由活动时间,孩子们可以在游戏室玩耍,也可以在图书室看书。玛格丽特女士要求我们每周写一封信给家人,虽然很多人的信根本无处可寄。我每次都会认真写信给母亲,尽管这些信都被存放在一个标着我名字的文件夹里,从未真正寄出过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。我认识了来自叙利亚的阿里,他的父母在战火中失散;还有来自尼日利亚的姐妹花,她们的父亲在英国工作却突然失去联系。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故事,都在这座大房子里等待着与家人团聚的那一天。
工作人员尽力为我们营造温馨的氛围。每周六晚上会有电影放映,每月还会组织一次郊游。但再多的活动也掩盖不了孩子们眼中的思念。有时深夜醒来,我能听到走廊里传来轻轻的脚步声,那是值班工作人员在巡视,确保每个孩子都安然入睡。
三个月后的一天,玛格丽特女士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。她告诉我社会福利部门终于联系上了我的母亲。原来她因为突发疾病住院,手机在匆忙中丢失,因此无法与我取得联系。听到这个消息我既高兴又担心,高兴的是母亲终于有了消息,担心的是她的健康状况。
两周后母亲出院来到寄养中心接我。当她出现在门口时,我们相拥而泣。玛格丽特女士站在一旁微笑着,眼中闪着泪光。离开时我回头看了看这座维多利亚建筑,突然意识到这里虽然不是我理想中的家,但在我最无助的时候给予了温暖的庇护。
如今多年过去,我仍然会想起在寄养中心的日子。那段时间让我学会了独立,也懂得了珍惜。每个孩子都应该有一个温暖的家,但当意外发生时,有这样一个地方能够提供暂时的避风港,或许是不幸中的万幸。这段经历塑造了今天的我,让我更加理解家的意义。